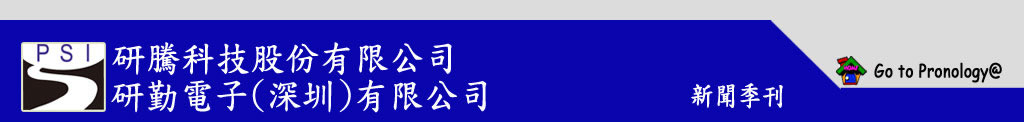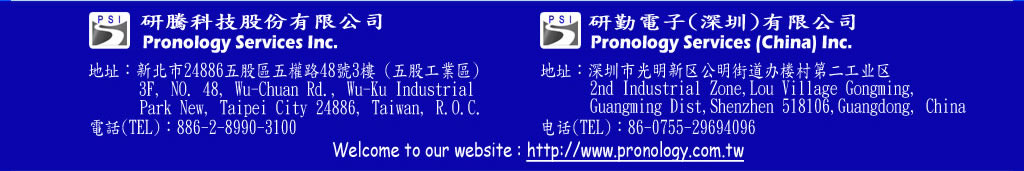在台灣像我這種五年級的學生,中國歷史是從小學到大的,可惜我讀書不得法,不知道歷史要搭配地圖來唸才能事半功倍的。真對歷史讀出一點概念,還是透過神鵰俠侶幫忙!不過,應付歷史考試是一回事,討論歷史上的特定事件又是另一回事。鑑往知來,在此寫寫對于明初三大案之一「空印案」我的看法。
可能很多朋友不清楚「空印案」是什麼?稍後會介紹。先談談我對「空印案」產生興趣的原因有二:首先,「空印案」主要是官員在作業規定執行有滯礙的情況下採取變通做法,在未暴發犯罪情事下就遭到大規模殺戮的特殊冤案。因冤案受責當然是令人遺憾的史實,但令自己心有戚戚的是在服役任職補給軍官期間也採取過幾乎一模一樣的做法,照樣是備好空白印鑑辦事,想到古時官員的際遇,心中不能沒有感慨!
其次,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王侯將相雖然英明神武,但能在二十五史中留名立傳的畢竟有限。「空印案」的主角是明太祖朱元璋與一大群晦氣倒楣的官員,但其中誤觸龍麟,導致大批官員或被殺或被流放的卻是一名叫鄭士利讀書人的勸諫奏摺。這個新鮮吧!居然和本人的名字完全同音,而他分析問題的觀點和我心中思路也頗為類似,因為我也常天真的以為講事實、說道理可以說服人。讀史至此,不禁懷疑自己該不是他轉世吧?(明史中有《鄭士利傳》,評價頗佳,幸甚!)
現在介紹一下「空印案」:主要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權力基礎穩固後,先後發動了三次死亡人數逾萬的政治冤案,分別是「藍玉案」、「胡惟庸案」與「空印案」。對明初歷史不熟的朋友,可以在百度中搜尋字串“空印案”http://baike.baidu.com/view/45464.htm 。為充篇幅,我節錄如下:明初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均需派遣計吏至戶部,呈報地方財政的收支賬目及所有錢穀之數,府與布政使司、布政使司與戶部的數字必須完全相符,稍有差錯,即被駁回重造帳冊,並須加蓋原衙門官印。各布政使司計吏因離戶部道遠,為免往返奔走,便預持蓋有官印的空白帳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該空白帳冊蓋有騎縫印,不做他用,戶部對此從不干預。洪武八年(1375)考校錢穀書冊,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以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下令嚴辦。而此時有位讀書人鄭士利為營救其兄,特上書皇帝,結果,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杖一百,戍遠方! 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以上是百度網站「空印案」的大致案由,其它資料對「空印案」的描述也差不多,依史料來看,應該可以確認整個案子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對各級官員抱持著強烈懷疑心理的產物。對涉案官員來說,處理錢糧業務既需面對時程的要求,也要掌握數字的精確,稍有不慎寫錯或算錯,也許很多天以來的作業就得一切重來。在傳輸科技還不成熟的年代,為了給公文重蓋一顆章往返京城與駐地少則百里,多則數千里,真的是有現實上的困難。因此採用預蓋印鑑的公文應該也是無可厚非的彈性做法,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也!初衷應該很單純的只是希望能在符合作業規定的前提下完成工作而己,而且這是從元朝延襲下來的作法,大家也照著做,照理說沒什麼問題,結果明太祖朱元璋得知後卻一口認定有舞弊事件而下令調查。讀書人鄭士利基於營救其兄而對於「空印案」提出幾點申辯與批評:第一,官方文書要有效,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而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印,是不能用來為非作歹的;第二,錢糧之數,必須縣、府、省到戶部,級級往上相合,只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一個確數,而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那麼就必須返回省府重填,勢必要耽誤時間,所以“先印而後書”只是權宜之計,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沒有明確禁止空印的立法,現在殺空印者是沒有法律依據的;第四,官吏們都是經過數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這麼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
鄭士利的建言聽起來很言之成理,可惜明太祖朱元璋看了奏摺後“覽書大怒”,下場就是一大堆認真負責的官員被拖出去剝皮實草,懸於午門,連鄭士利自己都被流放!
(明代的處分主要是針對官員,對讀書人和百姓的處分是不多見的!也許鄭士利是少數幾個…)
看完不幸的歷史,想到倒楣的同宗,不禁慶幸自己有機會生長在不以殺人為管理手段的年代!面對歷史,除了感慨曾充斥著血腥與懷疑以外,不如檢討如何應對因制度性的缺失而造成的意外,因此我分為二個方面思考這個問題。笫一、自古以來,雖然有部族分立治/帝王封建一直到民主政治的演進,但就組織運作來說,強調建立制度,依制度行政的精神與要求可以說是從沒變更過的。依制度行政,既保證了任務的達成,也避免了弊端的發生,但從另一面來說,制度是沒有彈性的。特別是執行制度時如果受限於門戶之見,要求各級單位提供完美文件,如前述的戶部要求數字必須完全相符,稍有差錯即被駁回重造帳冊等等,那各級單位各顯神通實屬意料中事!因此設計制度時既要考慮長久執行的可靠性,也要考慮讓執行單位可以因時因地制宜的變通做法,否則拘泥不化,只會對組織運作產生不可預期的傷害!
第二、對執行業務的官員來說,雖說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不過面對制度性的障礙,如前述為了給公文重蓋一顆章往返京城與駐地百千里等毫無效率可言的要求而言,身為承辦官員,我相信ㄧ定是憚精竭慮的苦思對應之道,而且當時ㄧ定也有允許體制內建言修正的管道。可惜官員的憚精竭慮戶部上級並不領情,言辭懇切的建言皇帝也聽不進去,因此不但事前不能改善作業困難,事後還造成事態惡化的反效果。也許,這就反證了「伴君如伴虎」這句名言的正確性。皇帝龍心大悅時就加官進爵,皇帝生氣時就殺人如麻,特別是還發明剝皮實草,懸於午門示眾等手段,真是對中國人發明創造的能力感到不寒而慄!面對這種視殺人為管理萬靈丹的皇帝,我也只能想起孔夫子所說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的教誨,趁早走人也許是這群身不逢時官員較佳的選擇!
時代走入二十一世紀,恐怖的帝王統治早己結束,歷史的迷霧也掩蓋了死亡的足跡,被論死的官員具體人數各家史料不一,常見的說法從數百人到數萬人都有,更多的則是杖責與流放。「空印案」死幾百人也好,死幾萬人也好,對六百年後的我,其實也只是數字上的差別。我掩巻嘆息,祝願前世因案罹難的官員可以放下心中的怨氣,也希望文明的歷程,不要再出現血腥與懷疑!
世立 2013/7/31 誌於深圳 研勤